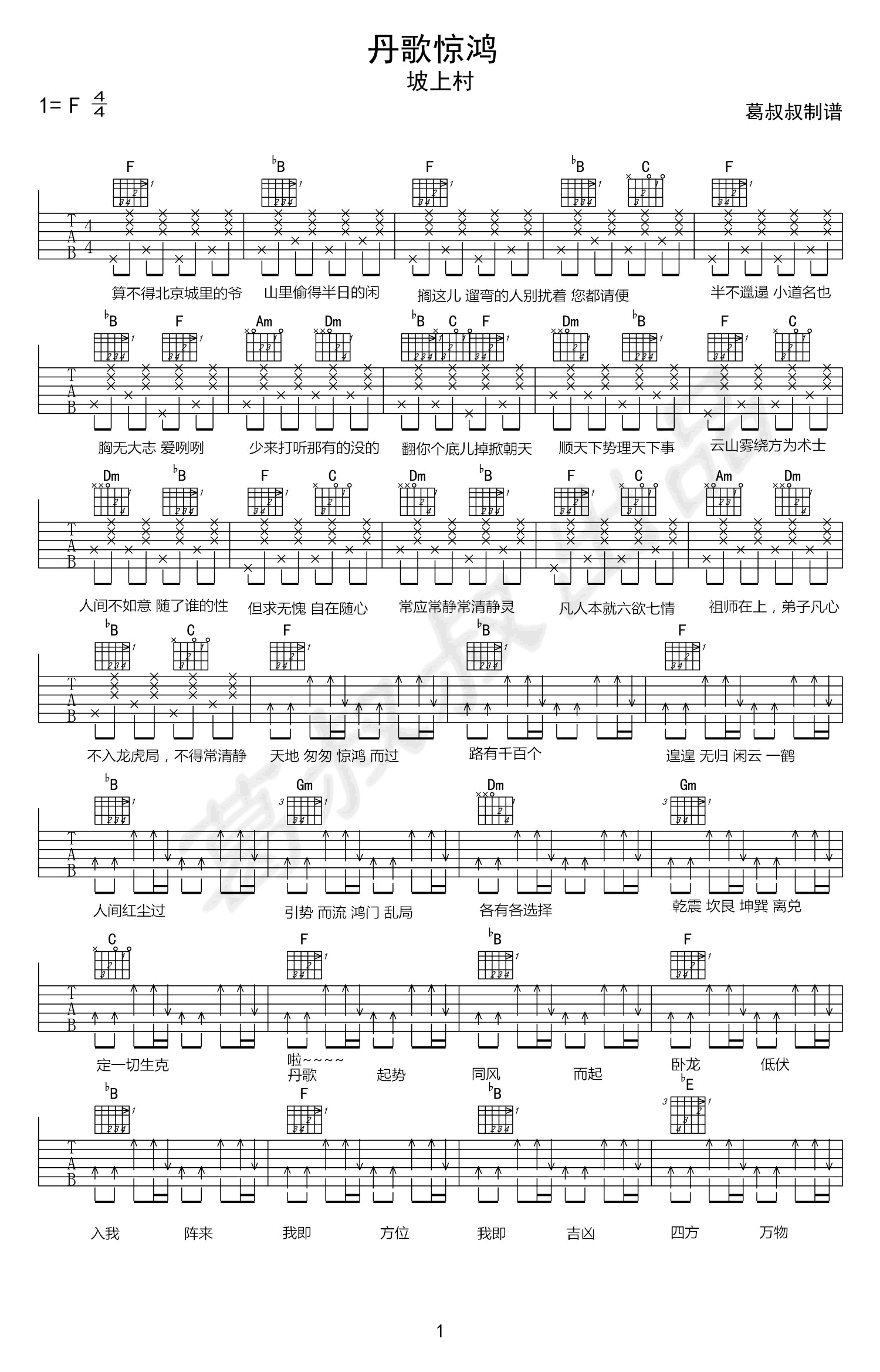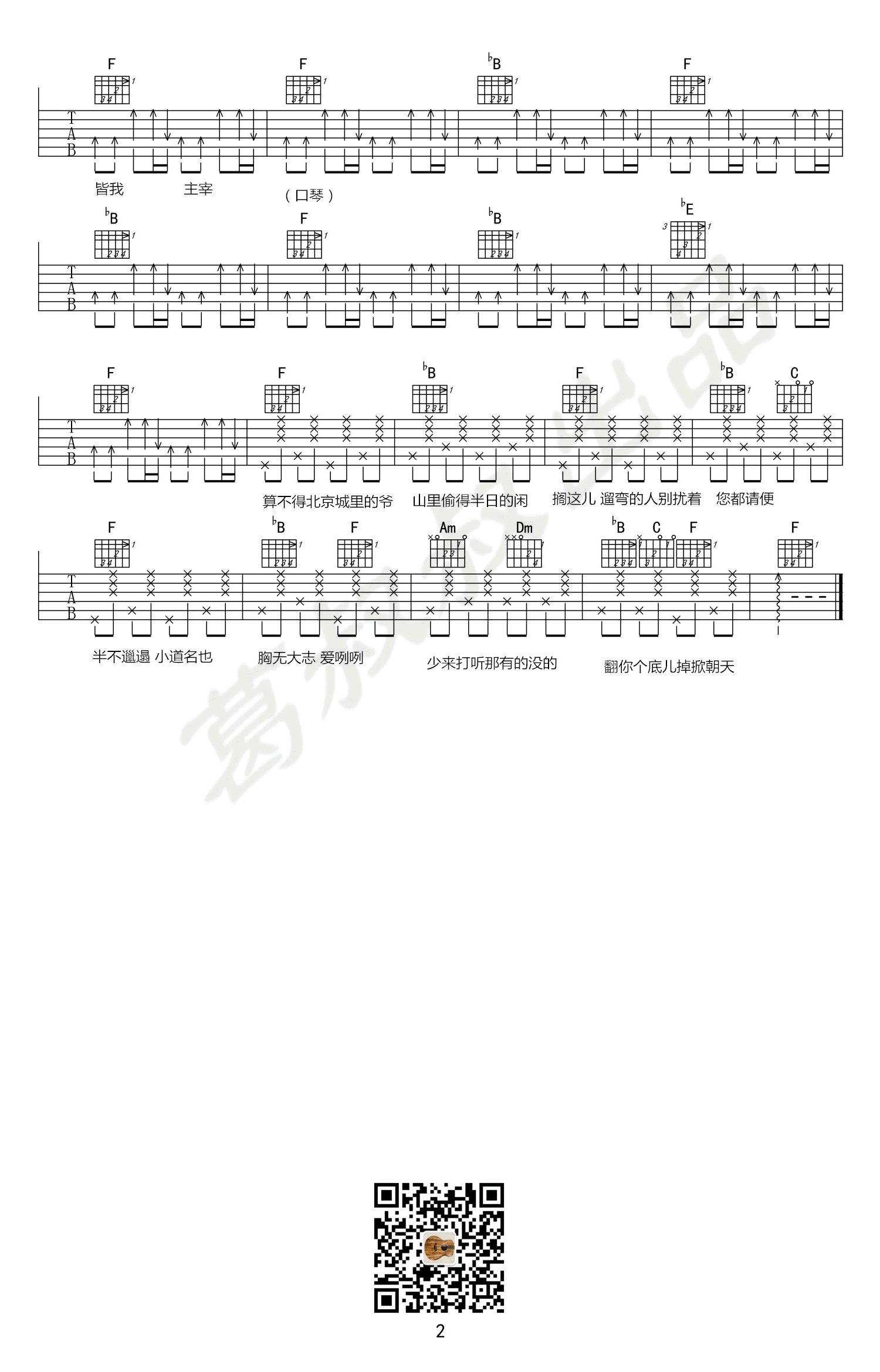《丹歌惊鸿》以传统戏曲元素为骨架,构建出虚实相生的东方美学意境。歌词中"朱砂点绛""水袖翻云"等意象形成强烈视觉张力,将舞台表演的刹那芳华升华为永恒艺术象征。"惊鸿"意象贯穿全篇,既指戏曲演员的翩跹身姿,又暗喻艺术生命在时光中的脆弱与不朽。通过"胭脂泪染旧戏文"的互文手法,将个体命运与戏曲传承的集体记忆相叠合,戏服上的金线牡丹成为文化基因的具象化符号。词作巧妙运用"三更鼓""铜镜昏"等传统意象群,在时空交错中展现艺术传承者"画皮画骨难画魂"的精神困境。末段"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"的时空蒙太奇,解构了演员与观众、历史与当下的二元对立,在"新词裁就付瑶琴"的开放性结局中,完成从技艺传承到文化创新的主题跃升。全词以戏曲为媒介,探讨了传统艺术在当代语境中的存续方式,那些被岁月磨损的唱腔身段,终将在文化记忆的维度获得重生。